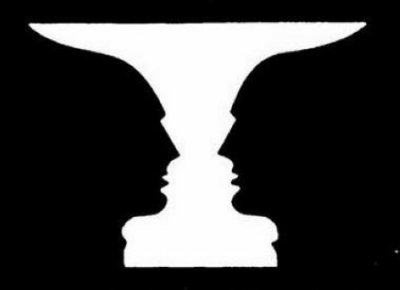心理学堂:人生大师的幸福观
发表于 2019-04-18 10:07
心理导读:我们也没有必要相信醒悟一定会给道德的泄气以鼓舞;因为事实是,那些看似泄气的其实是唯一传送那种强大到足可以接受它的勇气的途径;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因为它的正确而往往让人沮丧的真理仍然比最刺激的错误要有价值得多。但是事实上没有真理能够使人泄气,然而巨大的勇气的经过只是一个相关的表象而已。那些消磨人的意志的事情除了会使坚强的人变得更加坚强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作用。 ---www.tspsy.com

心理学堂:人生大师的幸福观
1、如何产生幸福的信念
为什么在公平不可能存在的地方要寻找公平呢?它到底在哪里呢?是保存在我们的灵魂里吗?它的语言是人类精神的天然的语言;但是这种精神必须学习新的单词才能在宇宙中旅行。公平是宇宙用以关注自己的终极的事情。它是吸引它的注意力的平衡器;我们所谓的公平只不过是这个平衡的转化而已,就像蜂蜜只不过是在花蕊中的甜水的转化一样。在人类的外部没有公平;在人类的体内也不能有不公平。人的躯体或许会在不正当的愉悦中狂欢,但是只有美德才能带给心灵以满足。
我们内部的幸福被一个廉洁的法官为我们度量了出来;而努力腐蚀这个法官的行为仍然会大大减小他最后刻在闪闪发光的刻度上的最终的真实的幸福的数量。有一个罗格宏将能够使一个无助的孩子苦闷,并使世界给生命的几个小时的机会都黯然失色,这已经足够不幸了;但是只有当邪恶在他体内产生幸福和平静时,不公平才产生,长时期花费在爱和中立上的思想和习惯的升华已经为斯宾诺沙和马可·奥勒留产生了。
一些轻微的智力上的满足或许是从罪恶的行为中得到的;但是即便如此,每一次错误的行为都会剪短我们思想的翅膀,直到它还剩下只能围绕自己爬行来消磨时光的长度为止。一个不公平的行为就证明我们还没有从我们本身抓住幸福。并且在那些把事情降低到它们最初级的要素的邪恶之中,我们应该发现,即使是坏事,它们也在寻求某种平静的方式,某种程度上的灵魂的升华。他们或许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并为或许会向他们走来的那种奢侈品而庆祝;但是它会使那些知道崇高的稳定和伟大的灵魂的复活的马可·奥勒留满足吗?在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海洋的孩子面前展现一个宽阔的湖泊,那么这个孩子就会兴奋地拍着双手,并认为大海就在它的面前;但是真正的大海依然真实地存在着。
或许存在这种情况,一个人将从他的日复一日的空虚、嫉妒或者冷漠中获得一个小小的胜利,他从中找到了幸福。能够看得更远的我们应当嫉妒他的幸福吗?我们应当为了他对于生命的清醒的认识、为了取悦于他的心灵的信仰、为了矫正他的注意力的宇宙观而努力吗?然而在这些事情之外是被建造的幸福河流的两岸;并且河流的宽窄和深浅取决于河岸的宽窄和深浅。他或许相信:有一个上帝存在,或者没有上帝的存在;所有的都会在这个世界终结,或者会延伸到下一个世界;所有的都是物质的,或者所有的都是精神的。他将如同聪明的人一样相信这些事情;但是你认为他的信仰的态度都是一样的吗?要毫无畏惧地直面人生;要接受自然法则,但并不是温顺的服从,而是像她的儿子一样敢于探索和提问;要在我们的灵魂中保持平静和自信——这些是产生幸福的信念。但是仅仅有信仰还不够;一切都要依靠如何去信仰。
我或许相信没有上帝的存在,因此我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的主要存在没有目的;在这个没有边界的世界的经济生活中,我的存在就如同逐渐凋零的花一样无足轻重——或许在我的精神信仰的深处,我相信所有的这些;你或许相信存在一个万能的上帝,他珍爱并保护着你,然而你的信仰或许是轻微的、渺小的。如果我的疑惑比你的信任更大、更高,并更迫切,如果这种疑惑更深入地刺进我的灵魂,如果它横亘于更加宽广的地平线上,如果它喜欢更多的事情,那么我就应当比你更加幸福,更加安详。如果我的怀疑所依据的思想和感情已经变得比支持我的信任的思想和感情更多更纯时,那么我的不信任的上帝将会变得比你依靠的上帝更加的巨大和舒适。因为,事实上,信仰和不信仰仅仅是一些空洞的词语而已;因此我们相信或不相信的并不是理性的忠诚、伟大和深刻。
2、幸福的地平线
我们不选择这些理由;它们是挣得的回报。我们所选择的仅仅是那些偶尔买到的奴隶而已;他们的生命是虚弱的;他们害羞地躲避着,寻求逃跑的机会。但是我们所选择的理由忠诚地在我们身边;他们是如此多的沉思的安提戈涅,我们永远依靠他们的帮助。没有哪种的理由能够被强迫塞进灵魂深处;因为事实上他们必须从最早的那天开始就在那儿萦绕,必须从孩提时代就在那儿接受我们的每一个思想和行动的熏陶;并且代表爱的生命的象征和爱必须围绕在他们的每一个方面。
当他们的根越扎越深——就像心灵的雾气渐渐飘散,出现了一个更加宽广的地平线时,于是这个幸福的地平线也变得越来越宽;因为只有在我们的思想和感情的世界里,我们的幸福才能自由地呼吸。它不要求物质世界,但是却发现我们开辟的精神领域是如此地狭窄;因此我们必须永不停息地拓宽它的范围,直到在那个自己开辟的领域里找到有效的养料能够使它在那里高高地翱翔为止。然后,幸福才真正照亮了最永恒的、人类最广大的部分;事实上幸福的所有的其他组成部分仅仅是这个伟大的幸福的未被意识到的碎片而已,当它在它面前反射并观看时,它就在它自身内部或者在它周围的其他碎片的内部发现它的无边的意识。构建的坚实堡垒……
我们不由自主地避开他们,是否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长者,虽然他们比我们年轻?……我们知道他们与我们不是同龄人,我们害怕他们,是否因为我们担心他们对我们静静地审视作出判断呢?他们的眼里已经表现出—种莫名的执着端庄;如果在我们躁动不安的时刻,他们表面上漫不经心的一瞥停留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会感到安慰和舒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是最为奇怪令人难解的一刻。我们会转身:他们正望着我们,庄严肃穆地对我们微笑着。有两个人,残酷的死神正在静静地等候他们——我清楚地记得他们的面容。但是一切都轻声轻气、小心翼翼,尽量使一切悄无声息地过去。他们受到一种致命的羞耻感的压迫,这种羞耻感几乎要把他们压垮了,他们似乎总是在为某种近在咫尺的、然而他们不知道的过错恳请宽恕和谅解。他们向我们走来,我们用目光迎上去;我们彼此拉开距离,默默地,我们明了一切,虽然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我们是否能够设想这样一种生存环境:一个真正聪明和高尚的人被置于一种环境中,这个环境的痛苦程度如同追求邪恶的人所遭受到的痛苦一样深刻。在这个世界里,做坏事会得到报应比做好事会得到奖励的可能性更大。然而我们必须在心里默默地忍受,在惩罚的背后大声地尖叫是犯罪的习惯,而美德则是在默默中回报自己,这就是幸福的花园围墙。在邪恶后面会出现可怕的大灾难;但是称之为美德的行为就是一个对生命的最深刻的法则的默默奉献;因此,毫无疑问,重大的正义的平衡似乎更容易在不光彩的行为下面而不是在光明正大的行为下面被打破。
但是如果我们勉强地认为“幸福存在于犯罪当中”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就有更多的理由来相信“美德的不幸”吗?我们知道,死刑执行人能够让斯宾诺沙横尸于死刑架上,那种可怕的疾病将不会给安东尼·庇护带来比格勒里尔和里干更多的宽容;但是这种痛苦是属于动物的,不是人类的,它存在于人类的身边。智慧事实上已经把她最小的妹妹--沉默,送到了命运的王国,同时也带来了她的使命,即在最小的限度内划定肉体痛苦的区域;但是在那个王国中存在着难以接近的区域,在那里灾难主宰一切。在那里一些受到打击的人将一直是不可复归的非正义的受害者;然而真正的智慧恰恰会因为在痛苦中的挣扎而被增强,并会得到自信和人格,这些或许会消失在更加神秘的品质中。只有当最后给予我们家园,而我们必须在我们自身寻找正义的模型时,我们才变得真正正义。是命运的不公正使人们又恢复到他们在宇宙中的位置。
如果他永远都要对他投以焦虑的眼光的话,那就像一个从母亲身边迷路的孩子一样,这很不合适。我们也没有必要相信醒悟一定会给道德的泄气以鼓舞;因为事实是,那些看似泄气的其实是唯一传送那种强大到足可以接受它的勇气的途径;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因为它的正确而往往让人沮丧的真理仍然比最刺激的错误要有价值得多。但是事实上没有真理能够使人泄气,然而巨大的勇气的经过只是一个相关的表象而已。那些消磨人的意志的事情除了会使坚强的人变得更加坚强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作用。
一个女人在给她的爱人的信中这样写道:“你还记得那一天吗?我们一起坐在面临大海的一个窗户前面,一起观看那陆续缓缓驶入海港的白帆船队伍,……咳!我怎样才能再重温那一天的美妙感觉呀!……你记得那只最后驶进港湾的接近黑色的帆船吗?你还记得我们分别的时刻是以最后一只小船,到达港湾作为我们起航的信号吗?我们或许能够从飘扬在桅杆上的那面黑色的船帆来找到伤心的理由;但是我们这对相爱的人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并且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思想是相通的时候,我们彼此均报以微笑。”是的,我们就应当这样做;即使当中找到一些其他的事情来驱除烦恼和伤心,就像我上面所引用的那个女人所讲的她的爱人吸引她的地方一样。随着大脑和心灵的充实,那些对不公正发出抱怨的途径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通畅了。经常提醒自己“我们究竟是这个世界上谁的传人”将是件好事,所有影响我们的事情必定是那些比我们想像中的最慈善的法律更加与我们的存在一致的事情。
或许已经到了人们把自己的快乐和骄傲的中心放在其他地方而不是自身内部的时候了。当这种观点在我们心里扎了根,并且越来越牢固时,那么我们就会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越来越意识到我们的无助;然而就在这一时刻,在这种压力之下,才产生了家园,我们成为这个家园的一部分;即使我们在家园背后进行反思,我们还是忍不住要渴望,就像年轻的忒勒马科斯渴望他父亲的臂膀的力量一样。我们自身的一些本能的行为激发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一种充满感情的、兴奋的惊奇: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训练我们自己把那些本能的行为看作是自然的行为呢?我们喜欢把我们的一点点理由的光泽扔进无意识中去: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所说的无意识在宇宙中付诸实践呢?我们与它的关联度并不比与其他的关联度低。
一位哲学家这样认为:“在人逐渐地熟悉了自身的力量以后,他的最高特权就是去认识他个人的能力缺陷。在冲出扼杀我们的无限和我们什么都不是的不均衡状态之后,我们的内心就升起一股庄严的感觉;我们感觉到我们宁愿被一座大山所压碎,也不愿意被一块小石子所打死,就像在战争中宁愿屈服于千万兵力的压力之下,也不愿意在单个对手面前倒下一样。既然我们的智慧就摆在我们的巨大的无助面前,那么它就会摧毁那些无助的锋芒。”有谁知道呢?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了那样一个时刻:那些已经征服我们的事情好像比那些我们屈从的另一些事情离我们自己更近了。
在我们所有的性格特征当中,自尊是最容易改变它的本质的一个,因为我们本能地意识到它从来就没有真正成为我们的一个组成部分。服侍在威严的国王身边的朝臣们的自尊很快就会在国王的无限的权力中找到更加灿烂辉煌的栖身之地;或许会降临到他身上的那种耻辱将会大大地降低他的自豪感,因为它是从一个君主的高度降落下来的。如果本性变得更加无关紧要的话,那么它将不会在广大的范围内出现了。我们那挣脱束缚的无限的感觉还不能够完全摆脱一个无限中的微粒,也不能摆脱它的一个公正的微粒;这样就会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保存一些东西,它宁愿在无限的世界里偶尔地哭泣,也不愿意在有限的世界里享受幸福。
如果命运永远不变地控制着智慧,那么毫无疑问,那样的一条规律的存在将会为它的优越性提供充分的证据;但是因为它是完全公正的,所以它是更好的,或许甚至是更伟大的;因为,灵魂的行动或许会丧失它的重要性,但是却会使宇宙的尊严得以扩展。圣人的庄严是不会丢失的;因为他对于自然的伟大同对于潜伏在人体内部的伟大具有同样的深刻的敏感性。为什么我们还要费力劳神地寻求无限呢?那些给予人类的尽可能多的东西将会跑到那些学会怀疑和好奇的人身边。
(作者:托尔斯泰 | 节选自《世界大师思想盛宴——人生大师哲理随笔》)
版权声明:标注来源“心灵花园”为原创,版权所有。本站部分资源来自互联网,转载之目的为学术交流与讨论,如因转载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
Copyright © 2010-2017 TSPSY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