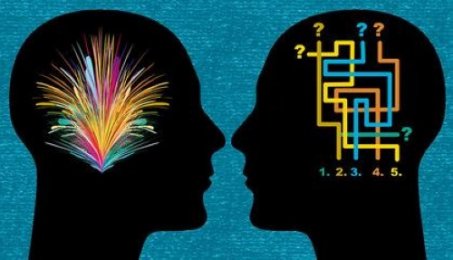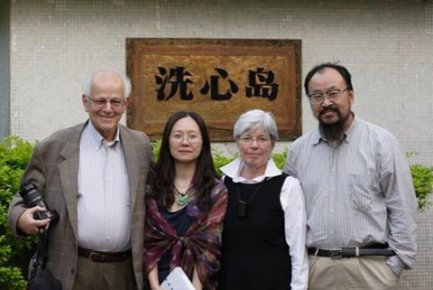心理咨询师:开启梦境的正确方法
发表于 2018-01-19 22:17
心理导读:我们不可误以为梦一定能表达这么明确的信息。即便经验最丰富的释梦者也会碰上解不开的谜。这种情形多半不是因为梦的本身没有意义可言,而是因为分析者的理解不够深入。心理分析对于分析师和病人一样具有教育功能。 ---www.tspsy.com

心理分析:开启梦境的正确方法
人的心灵又可以比为一栋房子,我们大多数人住在阁楼里,以下的房间连看也不看。所以我们过着不必那么受限的生活,我们的能力也大都荒废着不用。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当不止于此,把未能如愿的咎责归给外在环境-一没钱或没机会,却不知道必要的资源都可从自己内在取得。如果我们跟着梦走,梦会带我们到楼下的房间和地下室去,也能带我们去看房子外面的风景。阁楼以外的事物未必都是我们喜欢的,但是只要能走出去,就能体验冒险、发现、惊奇。这个想法实践起来并不简单,因为梦不用自我能轻易懂得的语言来表达智能。我们得从经验中学会理解这些传递信息的隐喻、寓意、梦境,并且欣赏这些以人类生存永恒主题新编的变奏。我们基于这一点可以说心理分析是一种教育步骤,接受分析者借此学会如何避开遗忘之树和天使在鼻子上拍的那一记。
这个步骤对某些人而言可能是艰辛且痛苦的经验,因为他们住的那间阁楼根本就是个要塞,是有坚强防御工事的城堡,堡里的发号司令官叫作“压抑”与“否认”。这两个生命的逃亡命者在不容潜意识和外在世界进入的城堡里躲着,慢条斯理地在安全的幽禁之中用例行琐事填着日子。只有到了夜晚,他们才漫游到城墙以外的世界去。在心理分析的早期阶段中,梦可以做这样的图解:做梦者待在一所监狱或集中营里;突然发现牢营的大门多年来一直是敞开着无人把守。心理分析师该做的是,为病人提供一个够安全的环境,让她(此处用“她”其实也包括“他”,泛指所有病人。根据我多年来的统计,女性病人与男性病人的数目为六与四之比,相信其他心理分析师的经验与我的大致相仿)走出自我防卫的牢笼,开始活在这个世界里。
我们不可误以为梦一定能表达这么明确的信息。即便经验最丰富的释梦者也会碰上解不开的谜。这种情形多半不是因为梦的本身没有意义可言,而是因为分析者的理解不够深入。心理分析对于分析师和病人一样具有教育功能。(许多心理治疗师已不再用“病人”一词,改用“案主”[ client或“接受心理分析者" analysand].。这是因为许多治疗师并非医学院出身,不便认同医病关系。我既是医生,不会有此种顾虑,而我也不认为“病人”的身份比医生就低一等。反之,我认为就教于我的人有“权利”做病人。治疗者与病人的关系是一种原型关系,一旦关系形成,治疗的程序已经展开。故意避免此种关系形成乃是相当严重的错误。)
长久以来我已养成习惯,若有人把梦讲给我听并问我有何意见,我一定先告诉自己:“我不懂这梦是什么意思。”之后我便可以着手研究这个梦了。
--荣格
我说过,我用的方法大体上是正统荣格学派心理治疗医师都在用的。这也就是说,每次心理咨询既是专业性质的会谈,也是社交活动。对待每位病人都要亲切而有礼貌,就好像平时对待有私交的友人一样。荣格特别强调:“应该当来人是正常的,以社交的方式对待。如果对方有精神官能症,乃是额外的收获。”接待病人的诊疗室应该如一般家里那样,气氛宜人,没有诊所的感觉。室内不放躺椅,分析医师和病人坐着一样的椅子。椅子舒适,两人保持双方都感到自在的距离。荣格主张这种安排,反对正宗弗洛伊德派心理分析师那种刻板形象:分析者坐在躺椅一端病人看不到的地方,冷淡沉默,偶尔吐出一句权威的话,不涉入病人的心理过程。荣格认为心理分析是一种辩证过程,是两个人之间的双向意见交换,双方参与的程度相同。
诊疗室虽然气氛平常,却是酝酿蜕变的神圣之地( temenos)不可亵渎。在这儿工作的一小时是恭谨慎重的,不容许干扰打断不接电话,旁边没有狗、猫、鱼,不许外人任意跑来敲门,这个轻松自在的氛围之中只衬着花、图画、书籍,外界的噪音减至最少。
就心理分析师的态度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不存有先入为主之相见。每位病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通则、武断意见、通用程序都派的病不上用场。荣格曾对学生说:“把理论都背熟。病人走进诊疗室之后,就把理论都忘掉。”心理分析师必须是专注的聆听者,让自己的想象把玩问诊过程中冒出来的每件事。开始就分析梦虽是常有的事,但通常最初的十至十五分钟都是谈问身外发生的事,如果讲到一些重要的题目是病人想细谈的,就接着谈下去,否则就转到梦的方面,反正不论题目为何,梦能说出来的总比自我能说的多。
假如病人记录了好几个梦,我就请她挑其中之一念出来。她边念我就一边改用自己的措辞写下梗概,这样我比较不会漏掉梦的细节,而且写成一份清楚的备忘录。专心听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梦的意象很容易引人入迷,稍不专心就会忘记聆听,跟着自己的想象神游去也。病人边念我边写,我便发现梦境能把我已知的片断事实串接起来,呈现出的新形貌使我顿然有所悟。不过我不会把这些尚未成熟的领会说出来,只是本分地问病人有什么联想,或有什么积极想象的成果。我该做的不是告诉病人她怎么了,而是协助她来弄明白。正如我让病人自己挑一个梦来念,我也鼓励她从梦中挑出她觉得很重要的部分,我先不说我认为哪一部分重要。这样做往往能进一步厘清事实。接下来进行“放大”,我和病人一同探讨这梦的个人的、文化的、原型的背景。按这个方式,无须特别解释梦的内容,梦的意义就会渐渐浮现,这意义也是医病双方有共识的。
有时候病人会把梦境的记录誊写成打字稿给我看,这样虽有用处,但我还是宁愿听他们亲口讲,因为讲的态度、语气都可能成为揭露真相的重要线索。在备有打字稿的情况下,我不必做笔记,只需在病人念的时候照稿子看一遍,一面把我认为重要的部分标示出来。这样也可以帮我集中注意力,约束我的想象。分析者该在什么时候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也没有一定的规则可循。我们凭经验学会拿捏时间,学会分辨自己的直觉有没有道理。假如你说话的时机不对,病人通常会告诉你,也许是当下就的直说,也许是用间接的方式,另讲别的梦。一定要等到医病双方都觉得这个梦已经处理完毕,我们才会开始谈另一个梦。由于梦的长度和内容不同,有些梦可能要花三、四次疗程来处理。常有的状况是,一整节问诊时间都用在谈一个意义深长的梦上,一个“重大”的梦则可能花掉好几节时间。至于一个梦该占用多少时间,应由医病双方一致的意见来决定。
病人述说的梦的质与量是因人而异的。通常只要病人投入了,梦就源源不断而来。但有时候病人会变得无梦可讲,倒不是因为她不再做梦了,而是因为她记不得梦的内容了。怎会这样呢?原因不一。也许是出于防卫心理:病人想把开始浮现的重要数据压抑下去,因为她不想面对这些部分。也许病人觉得对自己负责的担子太重了,宁愿处于被动,一切都扔给分析师(“不然我花钱找他做什么?”)也许是因为缺乏投入的意愿,不觉得梦境的含意有多么重要。也许是一种移情作用,把严苛冷淡的父亲形象投射到心理分析师身上,病人自己不想再做听话的女儿。不论如何,无梦可讲未必错都在病人。也许是分析师反应太迟钝或对以前的梦处理不得当,以致病人觉得被泼了冷水。
病人如果变得无梦可讲,心理分析师要格外谨慎,不要让病人自觉“坏了大事”而心生愧疚。是病人自己要来求诊,诊疗的时间要如何用,要讲些什么他们认为重要的事,应该由他们自便。我通常会等病人自己问起为什么没有梦了,我才建议分析可能涉及其中的原因。
在治疗初期,无梦可说的现象可能并没有隐含的动机。梦过即忘毕竟是常见的情形,但必须设法克服这种失忆。可行的方法将在以后进行详论。只要锲而不舍,就不怕记不住。
按我习惯的做法,第一次面谈要向初次来的病人说明把梦境确实记下来的重要性,并且教他们去买一本够大且悦目的笔记本来记录梦。我请他们把每个梦发生的日期记下,将梦写在摊开的笔记本的一边,空下对面这一页供记录联想和放大分析。我也要求病人记下每次面谈过程中有何种体会感想,以免重要的领悟流失,不但不能善加利用,反而掉入潜意识的无底洞。因此,病人来面谈之前必须做不少准备功课。荣格发现,接受心理分析成效最好的人,都是自己独立作业工夫下得最多的人。我也确信,花在记录梦境、联想、分析感想上的时间是绝对值得的。
(作者:安东尼.史蒂文斯 | 节选自《私人梦史》)
版权声明:标注来源“心灵花园”为原创,版权所有。本站部分资源来自互联网,转载之目的为学术交流与讨论,如因转载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
Copyright © 2010-2017 TSPSY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