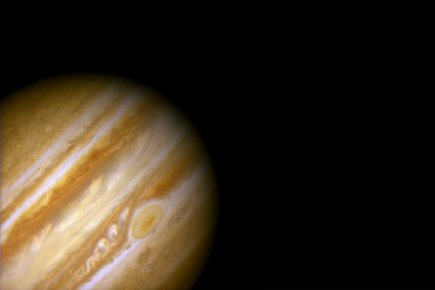心理咨询师:家暴的人还能改变吗?
发表于 2021-03-02 16:35
心理导读:在婚姻暴力中加害人处置方案的执行面上,多以「社会-文化」及「以家庭为基础的成因理论」为处置方案的基础,但在核心主题的呈现上,则显然非常重视个人层面的介入,其中包括认知行为、情绪疏导等等。至于暴力行为改变方面,在加害人自陈上,施暴次数有显着的降低,且暴力次数降低的情形远比控制次数降低情形为佳,表示辨别及改变暴力行为比改变控制行为容易。 ---www.tspsy.com

心理咨询师:家暴的人还能改变吗?
一、研究缘起
家庭暴力防治法自从1998年通过之后,现在又开始以司法的力量关切与重视家庭内的暴力事件与家庭成员的安全议题。且为了达到防止家庭暴力之立法宗旨,在第二条中明确界定「加害人处置计划」以期能透过处置,改变加害人的行为、停止家庭暴力的再发生。
1999年,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依法推出家庭暴力加害人处置计划以来,时至2012年的,处置计划是否一如预期地改变加害人的施暴行为,可说是众说纷云。Gondolf(2001)列举:多数的处置工作者均尝试举出一些例证,说明家庭暴力加害人处置的有效性,例如声称:「研究显示经过我们的加害人遇方案之后,只有14%的再犯率。」然而另一方面,有些强调受害人保护的单位却强烈地质疑对家庭暴力加害人处置的作法(Gondolf,2001)。究竟,「加害人处置方案」在整个家庭暴力防治网络中的定位为何?本研究拟从台湾执行加害人处置成效来探讨这个问题。
陈怡青(2012)曾提出进行家庭暴力加害人处置方案评估有四个好处:
(一)透过评估研究报告,可以为「成效」进行操作性定义。
(二)评估研究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回应实务上「有效」或「无效」的争议。
(三)评估研究有助于修正工作方法,以达到最佳的工作效益。
(四)透过方案评估检验工作目标的达成情形,有助于解决家庭暴力防治资源分配的争议。
要执行一个全面性的家庭暴力加害人处置成效评估研究是十分不易的,本研究的目的暂时先聚焦于婚姻暴力加害人处置的执行现况,在历经加害人处置方案之后加害人认知、行为与生活质量改变的情况,以及被害人在加害人处置前后的生活质量状态,以期能借以增进家暴网络下的实务工作者对执行处置计划的科学性的理解,做为未来思考与调整处置工作方法的依据。
二、文献探讨
(一)家庭暴力加害人处置的发展
家庭暴力加害人处置,或称「施暴者处置方案」(batterer intervention program;BIP)溯其源头始于北美。在1960年代以后兴起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连带发展出对受暴妇女的重视。从1975年到1995年二十年间,在美国产生的受暴妇女运动,聚焦在三个主要措施(Schechter, 1996),一是建置庇护所及危机支持服务,以因应对妇女及儿童受暴的危机介入;二是在法律上提升对妇女的保护;三是教育大众对家庭暴力的识知。在过程中,除了建置对妇女的保护措施并加以强化外,倡议者们也发现,纵使受害者在和相对人终止关系后,有不少的施暴者仍会对受害妇女进行恐吓,若对受暴妇女的支持与服务缺乏对暴力相对人的介入,那么对受暴妇女的服务无疑是受质疑的(Rothman, Butchart, & Cerda, 2003),故要停止暴力,必须要对施暴的相对人有所介入,在此氛围下,家庭暴力的加害人处置开始萌芽。
1970年代末期,在美国开始出现对加害人处置的方案。第一个对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的相对人服务方案为「EMERGE」,出现在波士顿(1977);同一时期在丹佛也有「AMEND」方案,以及在圣路易斯「RAVEN」方案,而不久后,着名的「Duluth Model」,以DAIP(Domestic Abuse Intervention Project)为基础,在1981年于明尼苏达州被建置起来(Rothman, Butchart, & Cerda, 2003)。值此之后,不同类型的处置方案被大量建置起来(Wiehe, 1998)。处置方案被大量建置的主因之一在于对IPV暴力者的「强制逮捕法」(mandatory arrest law )之设立。此法之源始于1984年,此年在康乃迪克的联邦地区法院(federal district court?)一个裁定案例,认为警察对一位受到先生残忍暴力的妇女没有做出适度保护,这促使州立法者思考如何让地区警察能有更强迫及限制的力量,在发生暴力事件时,来对抗施暴者并进行介入;再者,明尼苏达州的一个研究显示,强制逮捕对配偶攻击的暴力犯可有效遏止其再犯,基层医警察人员也认为这个策略很好(章光明, 2008),于是有许多州开始立法仿效。虽然强制逮捕法让警政系统取得法源,能自行判断受害妇女处于危机时,就能以警力来逮捕暴力加害人,以中断加害人立即可能的加害行为,但也造成IPV的加害人在法庭上的大量累积,因此形成法院后续处置的压力(Ford & Regoli, 1993),此一压力成为对加害人处置方案急速发展的重要推力(Simons & Lehmann, 2009)。到2003年时,在美国已累积超过1500个加害人处置方案(Adams, 2003),而2009年为止,约有150-250的加害人处置方案仍在美国各地执行(Carter, 2009 )。并且在美国的每一州及加拿大的每一省,都已经建置法院强制下的加害人处置形式(Austin & Dankwort, 1999)。
在美国,这些众多加害人处置方案最普遍的模型,即是Duluth Model,也多为各州发展对亲密伴侣暴力加害人处置标准时,其内在所服膺的模型。Duluth Model 是基于女性主义下的思维而来,认为男性在家长制(父权思想意识型态)之宰制下,试图去控制女性而产生家庭暴力行为。Duluth Model 有浓厚的心理教育色彩(Jackson et al., 2003),但也有学者认为它混和女性主义及认知行为原则,企图对加害人产生核心的改变,这些核心包括使加害人负起行为的任务,挑战及改变内在的信念/态度及教育加害人。因此在Duluth Model 下,暴力被视为学习而来的,而个人的心理性的问题及人格层面的处置,在进行过程中并不需要去考量(Simons & Lehmann, 2009)。
在这里产生一个问题,若是Duluth Model 后设的准则为真,即暴力的来源来自于文化上对父权意识的潜在学习,那么把握其原则,对加害人实施再教育,或是使用认知行为技术揭露加害人其中的内隐信念加以驳斥,或是让其探索「自动化思考」以明晰自己行为动力下的背后潜藏之认知内容,当可有效改变加害人的态度、价值观以至于后续行为,不再对受害人施予暴力。事实上,Duluth Model 的成效争议仍不断,有的研究指出没有证据显示Duluth Model 在加害人的态度改变上有任何的效果,也有研究指出,在加害人行为或态度上没有任何变化(Jackson et al., 2003)。但也有研究指出这种心理教育性的加害人处置介入有不错的效果,比如在罗得岛区的研究,其加害人处置的核心是40小时心理教育性的课程,对2006年到2010年接受加害人处置者进行分析,认为在监督机构和法院沟通良好及合作的状况下,加害人处置成效良好(Houston, 2011)。
对Duluth Model 成效的争议,让我们思考亲密伴侣暴力的成因是否并非全如Duluth Model 所代表「DAIP」所预设的--暴力的源由在社会及文化层面。是否除此之外,另有成因?在另一方面,对个人行为的产生,往往可在理论角度上,由三个层面的各成因来探讨,即为「社会-文化的成因理论」、「家庭为基础的成因理论」及「个人为基础的成因理论」(Healey, Smith, & O'Sullivan, 1998):
1.社会-文化的成因理论:认为暴力来自于文化的层面,如父权意识型态。在此文化价值下的男性,可合法地对女性施予权力控制,而在其中导致使用暴力手段。故对应下的方案处置核心在于对加害男性施予教育及建立两性相处技巧,使再社会化,以强调在亲密关系中的平等。
2.「家庭为基础的成因理论」:认为暴力行为来自家庭的结构及家庭互动上,并非在家庭中的单一个人上。家庭系统介入,强调沟通技巧的建立,甚至包含夫妻谘商以保全家庭,都可能是介入的方案。但此一介入型态多不为实务者所运用,因为许多实务工作者反对在处置中不去归责加害人并确认受害者。而且不小心使用的话,还会让受害人陷于险境。故美国有20州的处置标准中载明,禁止伴侣谘商为主要介入模式。
3. 「个人为基础的成因理论」:把暴力归因于心理层面问题,如人格违常、或童年经验、或生理倾向。心理治疗、认知行为治疗、依附下受虐之心理介入为其解决之道。
相应于三个层面的暴力成因理论,也发展出三类不同的介入模式及策略(Healey & Smith, 2000)。相应于「社会-文化成因理论」为「女性主义途径」;相应于「家庭为基础的成因理论」为「家庭系统模型」;相应于「个人为基础的成因理论」为「心理治疗途径」。此三类介入模式,各有被批评之处。比如,「女性主义途径」忽略个人可能在童年的受虐经验,并视所有男性可能都会施暴,而过度面质易导致自我挫败感而使加害人减低进入处置意愿等‥;「家庭系统模型」的伴侣谘商型式,如果让受害人坦白表达抱怨,则可能导致受害人陷于危险。而「心理治疗途径」则被批评,如「难到要等到内在问解决才能终止暴力吗?!」,无法解释在不同的关系下就没有暴力行为,以及忽略文化上偏于男性的父权意识型态之影响。
Boonzaier (2008)把「家庭」此一层面,修改成「关系层面」(Relationship level),并进一步的统合这三个层面而成为生态模式,各层面有阶层涵盖性关系,以解释相对人对妇女施暴的多因性,如「个人层面」涵盖最小,个人因素多为个人心理特质,影响未来成为加害人或被害人的可能性,包括酒精药物使用、个人在原生家庭的暴力经验以及年纪‥等。而「个人」置身在「关系」中,「关系层面」涵盖个人与个人间的互动情况,包括家人朋友的影响、伴侣冲突、是否同居、关系权力‥等。而关系的两(众)人皆生活在该「社会文化」中,该社会文化是否鼓励暴力的氛围,以及诸如社会经济状况(失业、贫穷)、教育水平、文化差异、种族、父权思想‥等,故「社会文化层面」是最大的背景。
使用生态学多因解释的方式,就可以针对其成因,发展出不同介入的重心及方法。
在WHO的2003调查,Rothman et al. (2003)指出,就国际间的比较,在美国及英国之外的国家,其处置方案,有高达73%采用性别观点(亲女性主义,pro-feminism)做为家庭暴力的成因,27%则是采取心理病理学,即行为、情绪、认知问题或童年经验做为家庭暴力的成因观点。在发展中国家的处置方案,有88%采用女性主义模型;而在发达国家,则是63%采用女性主义模型。但有趣的是,不管视暴力的成因观点为何,大部份的处置方案都涵盖相似的主题。
我们可以用生态模式当做骨干,把一些知名及已被认可的处置方案整理,并填入相对应的位置,如此做可以清楚地呈现暴力的危险因子。
此外,除了暴力行为之外,家庭暴力的其它复杂面向也应一并地被考虑进来,Mills认为「长久以来,女性主义在回应亲密虐待时,一直不愿恰当地理解家庭暴力的复杂性与亲密性。因此,发展恰当的女性主义理论乃是目前最实际的任务。」(2004)。Mills也尝试把修复式正义的概念融入在对加害人的司法处置中(Mills & Grauwiler, 2004)。在2012年2月,Mills博士曾率领美国纽约暴力与恢复中心同仁来台,推广修复式正义观点下的和平圈加害人处置方案,主张对关系的疗愈为处置重点,而非传统的处置重点-对加害人的处罚、引发羞耻感。
不少学者亦反省标准化的处置方案(如Duluth Model)是否适合所有亲密伴侣暴力加害人,即「one-size-fit-all」的问题,近来的趋势显示,亲密伴侣暴力的「男性加害人们」其实是具多元异质性,这也间接呼应对加害人进行类型学的分类研究有适当基础。Stuart(2005)主张不应只用单一介入标准,不应只对加害人进行评估,处置时应对加害人、受害人两造及其互动做评估,也对两造进行处置。
总之,美国的加人处置方案基于实证研究的不同发现,显然仍走在一个转化与改变的阶段。处置模式的有效性虽被肯定,但在实证与实务的领域仍一直在检验与修正的过程中。如何辨别加害人处置的适合性?实证研究的方法提供我们一个策略,台湾的家庭暴力加害人处置推行已有13年之久,透过成效评估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思考与再出发。
(二)目前台湾执行加害人处置的现况
在台湾家暴加害人处置模式上,依据王兹繐(2008)的分期,在1998年家庭暴力防治法通过以前为「酝酿期」,并没有加害人处置计划,此时以妇女保护为主。在1998-2001/02时期,为「家庭暴力法制化」时期,在2001年2月修正公布并建立相对人鉴定机制,此时保护令的核发及保护令中裁定相对人处置计划成为保护受暴者及预防暴力再犯的重要司法措施。但因准备尚未完整,1999-2001年所核发的所有保护令中,裁定加害人处置计划者,仅占1.8%,而占通常保护令的3.2%。在2001/01到目前,为「处置方案多元发展」时期,其中一项重要的因素是2001年8月全面实施家庭暴力相对人裁定前鉴定制度,法官在裁定保护令中的相对人处置令时有了专业意见的参考。
在对加害人实施处置计划中,依其形式,可分为个别处置及团体处置。在王佩玲与黄志中(2005)的调查中,个别处置占6成,团体处处置占2成,其余2成为两种形式兼具。在处置内容上,个别处置的结构性较弱,而团体处置的结构性较强,往往已规划既定之主题。团体处置的实施周数介于8-12周。
目前在台湾主要家庭暴力加害人处置团体相当多元,依不同县市及不同处置机构及处置者而发展不同,目前发展较完整与成熟的包含下列几个(王佩玲与黄志中,2005;王兹繐,2008;陈怡青等,2012):
1.高雄市认知教育团体
2.台北县(新北市)家庭安全认知教育团体
3.高雄县慈惠医院认知辅导教育团体
4.沟通分析学派取向的团体治疗模式
5.国军北投医院认知辅导教育团体-整合性别平等与人本主义学派之辅导教育模式
6.嘉南疗养院认知教育与情绪支持团体
7.新竹县市认知教育团体
8.以再犯预防及现实疗法为取向的认知行为疗法
目前台湾大多数的团体的理论依据大都结合女性主义及认知行为治疗模式为主,再视模式之不同,结合现实治疗、沟通分析、家庭动力、冲突理论、再犯预防…等模式,我们可称之为「多元的综融模式」。
二、家庭暴力加害人处置成效
加害人处置是否有效?成效如何?一直是个核心主题。在前一节的文献探讨可知,在美国最初的发展,由女性主义思潮下的受虐妇女运动,推动以女性主义为基础的加害人处置模式。此一模式先有理论,再往下形成具体的实践程序及方法,然后运用在亲密伴侣暴力的男性加害人身上。此时,虽有为数不少的成效评估的研究,但其结论一直有所争议,多因方法学上的问题而争议,诸如对成功的实际行为为何、成效是否随时间变化、是否使用控制组或对照组、所控制变项是否影响介入成功率等(Eisikovits & Edleson, 1989 ,引自 Wiehe, 1998)。
Lehmann & Simons(2009)统合Labriola, Rempel, and Davis(2005, 引自 Simons & Lehmann, 2009)提出有效性研究的四代区分,把对加害人处置方案的有效性研究区分成四代:
1.第一代研究多基于对有效性的探索,而没有使用对照组。故其结论无法确实地回答行为改变和处置的关系。
2.第二代研究使用准实验设计(quasi-experimental),比较接受处置方案的加害人与没有接受处置方案的加害人,但因在两群加害人先前条件因素不相同,故其结论也无法有效确认。
3.第三代研究使用随机分配的过程设计,这个被视为黄金定律的评估方法,在实务执行上有困难并有所争议。其结果显示,不论在对妇女的再犯及态度上、对暴力的信念、在组间比较上接受处置后的暴力程度和认知改变,在上述变项上,两组的差异很少。
4.第四代的研究使用后设分析(mata-analysis),三个后设分析的结果显示,处置方案成效不大。仅比单纯比法院逮捕的效果好一点;不论在Duluth/女性主义及认知行为方式,其成效都不大。
Babcock, Canady, Graham, and Schart (2007, 引自 Simons & Lehmann, 2009)认为成效研究的意涵告诉我们哪些方案效用有限,而非处置方案不必要或无效。并进一步表示,比起只有被法院逮捕认罪而没有进入处置方案的加害人,那些有多进入处置方案的加害人,其相对的妇女,多5%免于再受到攻击。
但总体来说,对肢体暴力的攻击,在经过加害人处置方案后,多可能降低攻击的机率。在接受加害人处置方案后,有60%-80%的加害人不再对其伴侣出现肢体暴力,但非肢体的施虐仍然处在较高的比率。(Buttell and Carney, 2004, 引自Boonzaier, 2008)。
在WHO于2003的研究报告中(Rothman et al.,2003),则是肯定加害人处置计划在阻止加害人进一步施虐有适度的效果。而在美国及英国,在完成处置方案的加害人比起没能完成处置方案的加害人,有50%-90%的比例在六个月到三年的追踪上,依然维持在没有暴力的行为上。比起中断处置的加害人,能完成处置的加害人,约有三分之二的比例不太可能再对伴侣施以肢体暴力。
在台湾,行政单位认为现阶段处置量太低,尚无法看出成效,且不应放大处置成效(王兹繐,2008)。因处置方案随各地各机构及各处置人员产生不同形式及样貌的处置方案,其间没有一定标准化的方案,反而避开在美国所谓「one-size-fit-all」的状况。也因此处置成效,不能以通称来称呼「加害人处置成效」,而应以「加害人的…的方案处置成效」,较为适切。兹以各地区方案的处置成效,略说如下:(摘自王兹繐,2008)
1.以再犯预防以及现实疗法为取向的认知行为疗法:完成处置与未参加者两组前后的肢体暴力皆显着减少。同居者的危险程度比分居者与失联者低,而同居者所遭受的精神或身体暴力皆比失联者低。
2.台北县(新北市)家庭安全认知教育:在态度、认知、语言方面有显着进步,而且加害人与配偶的相处也不再有肢体暴力行为。
3.高雄县慈惠医院的认知辅导教育团体:有近六成(58%)完成处置计划,一成中断(11%),一成拒绝接受(11%),二成是逾期无法完成。由其经验发现该县中断处置者仅约一成。
4.沟通分析学派取向的团体治疗模式(台中、屏东):在参与度、个人功能、暴力控制、问题解决与两性平权五个向度,在前后测上均有显着差异,确实有助于改善加害人暴力认知与行为。
5.国军北投医院-整合性别平等与人本学派之辅导教育模式:在非暴力认知行为与处理策略均有效改善。
6.嘉南疗养院-认知教育暨情绪支持团体:实验组加害人的认罪倾向增加,对照组认罪倾向无改变。情绪方面,两组更为负向。团体的过程确实可以使加害人获得支持,在团体中也有学习模仿的对象,可达到团体欲提供教育与支持的目标。
除上述的处置成效依不同方案而有不同讨论方向之外,还有另一种以施暴者样态来进行分析的方式:Kelly and Johnson (2008)则是针对亲密伴侣暴力进行暴力行为上的分类,此分类考虑伴侣间的动力、脉络和结果,把亲密伴侣暴力行为分成四类:「强迫控制型暴力」(Coercive Controlling Violence),此型即为众所周知的权控型暴力;二是「暴力反抗型」(Violent Resistance),暴力的目的在于反制对方的暴力,常是针对第一型的暴力反应,许多女性对男性的暴力行为多属此类;三是「情境型的伴侣暴力」( Situational Couple Violence),此类的暴力没有长期权控的动力基础,多因情境性的冲突而引发暴力的动机;第四个是「分离-促发性的暴力」(Separation-Instigated Violence),此暴力多在分手的脉络下,不断发生的暴力行为。它时常是在分手过中所产生的「情境型的伴侣暴力」之进阶版,也可能后续形成「强迫控制型暴力」,甚至在相对人感觉到分手危及其控制感时,有可能发展成凶杀的风险。Kelly and Johnson (2008)亦提出处置有效性争议的问题,认为有效性的争议,可能是因为对不同类型的暴力加害人效益不同所致,指出最近一个约200位男性加害人的处置研究,有高达77%的情境型的伴侣暴力加害人可以完成处置方案,而属于强迫控制型暴力的另两组加害人,完成处置方案的比率分别是38%和9%。再者,在15个月的后续追踪上,在情境型的伴侣暴力加害人中,只有21%的配偶报告有再犯。而属于强迫控制型暴力的另两组加害人再犯比率则是42%及44%。
由处置成效的讨论上,可知其蕴含的问题相当复杂,我们大致可从结构上区分下列几个涉及面向:
1.加害人面向:加害人异质性的问题,类型学的努力想区分出不同的类型。再者,加害人的社经地位、教育程度、童年经验、酒精药物使用、对婚姻的想象与信念、暴力事件型态及严重度、对暴力事件的解释、改变的动机‥等。均可能影响成效。
2.处置人员面向:处置人员特质、处置人员性别、处置人员经验、熟悉方案的程度、对暴力事件的立场、自身家庭经验的影响、对待加害人的态度等,也须考虑进去。
3.处置方案的形式与内容:不同方案的着力点、时间及频率的变项、后设哲学基础与实践应用的方法、与司法人员的权责分工、和其他措施的网络关联…等。此为最常被讨论及研究的面向。
4.受害者面向:受害者对加害人的态度、受害者对加害人的关系的评断、期待与展望、受害者个人对暴力的感知判准、受害者的特质、受害者对此一暴力案件的看法与后续期待…等。此面向,亦可能影响对成效的评估,毕竟加害人处置方案的重要目标在于停止及预防对受害者的暴力。
在这四个面向交织组合下的所产生的处置路径,有可能有的极有效果,有的则无。在此我们可用共同因素观点(common factors perspective)的pantheoretical model来看在处置下的「改变」之变异分析(摘自 Lehmann & Simons, 2009),案主之所以改变:
1.有40%来自案主自身的疗效因子,比如性格优点、资源、因应技巧、动机、生活区域、社会支持等。
2.有30%来自「案主/治疗人员」的关系,包括治疗关系质量。
3.有15%来自治疗者是否带给案主希望感的态度。
4.只有15%是技巧及模式的因素。
由此观之,致力于处置关系质量及带给加害人未来的希望感,比起模式的运用,更能促使加害人改变。
美国司法部下的国家司法研究院及家庭暴力预防基金会及某私人基金会,在2009年12月时邀请美国境内家庭暴力及加害人处置专家齐聚华盛顿举行圆桌会议(Carter, 2009),与会的专家学者均同意加害人处置方案对一些男性是成功的,但对多少比例的男性因参与方案而停止暴力则没有共识,也没有讨论出在实务上最好的机制是什么。不过对形成加害人处置方案,则确认七个重要元素(摘自 Carter, 2009):
1.和其他人及组织形成伙伴关系以强化各权责性并提供一定范围的服务
2.和法院密切合作并善用缓刑期以监控法庭强制转介到加害人处置方案之加害人
3.处置方案要有扎实基础,包括对处置人员持续的训练和督导、政策的执行须和实务一致
4.不只限于法律视野下转介的处置方案,可进一步整体考量,发展能和社区接合并运作方案
5.从成人幸存者及儿童的观点及需求来对介入及方案进行修整
6.使用危险评估及危机管理的方法,对个别男性施暴者提供更有效的介入
7.尽速让男性能投入承担「父母」及「丈夫/伴侣」的角色
由上述整理可见,有关加害人处置成效的面向是十分复杂的,很难从单一一个角度来总括所有的结果。因此,从不同的轴向出发,一一讨论与检视加害人处置成效是效是有必要的,本研究将从处置方案、处置人员评估、加害人暴力行为与被害人生活质量等方向来进行资料搜集,以期能对台湾的婚暴力加害人处置有更深入的了解。
(作者:陈怡青;李维庭;张纪薇;李美珍 | 来源:tap.org)
版权声明:标注来源“心灵花园”为原创,版权所有。本站部分资源来自互联网,转载之目的为学术交流与讨论,如因转载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
Copyright © 2010-2017 TSPSY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