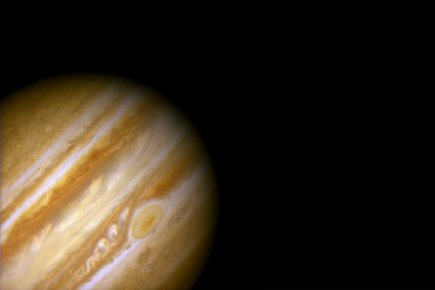心理疾病: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治疗2
发表于 2019-04-28 11:26
心理导读:尽管创伤性经历可能已经过去多年,人们通常依旧极难谈及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身体会重新体会到恐怖、狂怒、无助以及想要战斗或逃跑的冲动,但这些感受都几乎无法言喻。创伤在本质上将我们逼到了理解能力的边缘,我们无法用在日常体验中发展而来的语言描述创伤。 ---www.tspsy.com

无法描述的恐怖
最出乎我们意料的发现,是一个在前额叶皮层,即布洛卡区发现的白点。在这里,意味着这片脑区的活跃下降。布洛卡区是脑中的语言中心,中风病人的这片大脑区域通常会因为供血中断而出现问题。如果布洛卡区不能正常工作,你就不能让你的思想和感情变成词语。我们的扫描结果表明布洛卡区在闪回触发时不能正常工作,换言之,创伤对大脑的影响可能类似于大脑的物理损伤,例如中风。
所有的创伤都是先于语言的。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抓住了这种无言的恐怖。当麦克德夫发现国王被谋杀的尸体时,发出惊叫:“啊,可怕!可怕!可怕!不可言喻、不可想象的恐怖!”在极端的情形下,人们可能会喊出粗话,或呼叫母亲,或发出嚎叫,或直接吓呆。暴力犯罪的受害者或者事故受害者在急诊室中呆滞地坐着;受过创伤的孩子拒绝说话;照片里,参战士兵空洞的眼神无言地注视着虚空。
尽管创伤性经历可能已经过去多年,人们通常依旧极难谈及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身体会重新体会到恐怖、狂怒、无助以及想要战斗或逃跑的冲动,但这些感受都几乎无法言喻。创伤在本质上将我们逼到了理解能力的边缘,我们无法用在日常体验中发展而来的语言描述创伤。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能够谈及在他们身上降临的悲剧。大多数幸存者,或多或少,就如同第一章所叙述的退伍士兵,得出了他们叫作“表面故事”的一套说辞对付其他人,来解释他们的症状和行为。然而,这些故事几乎不会触及内核。要将这些创伤性经历变成一个有始有终、完整流畅的叙述,是极度困难的。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记者,例如著名的CBS记者埃德?默罗(Ed Murrow)也难以叙述他在1945年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放时看到的场景:“我求求你们相信我所说的:我仅仅是报道了我的一小部分所见所闻而已,而我所见的大部分都超出了语言能描述的范围。”
当语言无力描述时,图像就会以噩梦或闪回的方式萦绕着我们的大脑。与布洛卡区的激活不足不同,布罗德曼19区(视觉皮层)高度激活。这一区域负责接收一开始进入我们的大脑的图像。我们惊讶地发现,即使创伤性经历已经过去多年,这一区域的大脑皮层仍然持续激活。在正常情况下,布罗德曼19区的激活会迅速转移到其他大脑皮层区域,开始解读视觉刺激。我们又一次发现,大脑好像重新面临实际发生的创伤性事件一样。
我们将会在第12章讨论到创伤性记忆。有关创伤性经历的记忆碎片独立于创伤性经历的故事本身,记录在大脑里。例如声音和触感,当人们再次体验到类似的感觉,就很有可能再次把创伤性记忆的闪回鲜活地带回他们的意识中。
转到一侧大脑
扫描结果通常发现,在经历闪回时,被试仅有右半边的大脑被激活。今天,大量科学和流行文献表明左右脑有不同分工。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一些人试图将人分成“左脑人(理性、逻辑的人)”和“右脑人(直觉、艺术化的人)”,但我当时并没有留意这一观念。然而,我们的扫描结果清楚表明,创伤会激活右脑,而左脑激活不足。
既有的研究告诉我们,左右脑是不同的。右脑是充满直觉和感性的,掌管视觉、空间和触觉;左脑掌管语言、顺序和分析。左脑负责叙述,而右脑负责体验。右脑通过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体验到感情,例如歌唱、咒骂、哭泣、舞蹈或模仿。右脑是子宫中首先发展的部位,它负责母婴之间的非语言交流。左脑在儿童理解语言和学会说话之后开始活跃,这让他们可以给事物命名、比较不同的事物、理解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将他们的主观体验告诉其他人。
左右半脑也通过完全不同的方式处理过去的经历。左脑记住事实、数据以及描述事件的词语。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为“将我们的体验按顺序进行解释”。右脑储存有关声音、触感、气味和情绪的记忆。类似的声音、面部表情,还有肢体动作、去过的地点,这些记忆都会自动触发右脑记忆。当右脑调动记忆时,人就可以体验到几乎与真实相同的感觉。例如,当我们向他人描述我们的爱人时,我们更有可能会因为她长得像我们4岁时喜欢的阿姨而深深动容。
在日常情况下,即使是在那些声称自己更倾向于一侧大脑的人身上,人类的双侧大脑基本上都合作无间。然而,如果有一侧的大脑停止运转,无论是暂时的中断还是像早期大脑手术一样完全切除一侧大脑,都会导致大脑的功能障碍。
左脑激活不足会降低我们将经验以逻辑顺序组织起来、将感受和感知变成语言的能力(位于左脑的布洛卡区在闪回时会激活不足)。如果我们无法按照某种次序将经验组织起来,我们将无法判断事情的起因和后果、无法预测行为的长期后果或为将来做长远打算。人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失去理智”,事实上,他们在经历大脑执行功能的损失。
当外界勾起创伤幸存者的创伤性记忆时,他们的右脑会反应得好像创伤事件正在发生一样。由于他们的左脑功能受损,他们不能很好地区分过去和现在的体验——他们直接陷入了混乱、恐怖、愤怒、羞愧或惊吓中。从暴风雨一般的情绪反应过后,他们可能迁怒于一些人或一些事,例如你迟到10分钟、把土豆烤焦了,或者你“从来不听我话”。当然,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这种倾向,我们在事后可以察觉并承认这种错误;但创伤让这种自我觉察不复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研究发现了这一机制的原因。
卡在战斗或逃跑反应中
我们逐渐明白了玛莎的扫描结果。13年过去了,她有关这次创伤的感官记忆——例如有关这次事故的声音和图像——仍然牢牢地待在她的记忆里。当这些记忆浮到表面,她如同再次回到医生告知她的女儿死亡的那个时刻,警觉系统疯狂警告,心跳和血压陡然上升,这一应激反应经过了13年仍然未消退。
肾上腺素是帮助我们在危险面前逃脱或战斗最关键的激素之一。当被试听见有关他们创伤的叙述时,肾上腺素的上升让被试心跳和血压大幅上升。在正常状态下,人们应对危险的方式是暂时升高他们的压力激素。当危机过后,激素回到正常水平,生理状态也回归正常。相反,对于创伤后的人来说,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让激素回到基线水平,而且面临轻度压力刺激时,他们的激素压力水平也会飙升。较高的激素水平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包括记忆和注意力问题、易激惹和睡眠障碍。对于每个人而言,这也有可能带来很多长期的健康问题,尤其是他们的身体系统最脆弱的那部分。
另一种应对危机但我们的扫描无法测量的方式,是否认。他们的身体记录着这些威胁,但他们的意识上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尽管他们学会了如何忽略大脑的情绪信息,但身体的警觉信号并不会停止。大脑仍然处理着情绪信息,压力激素继续传递着信号,让肌肉变得紧张以准备行动,或因崩溃而吓呆。这一生理反应持续进行着,直到他们表现出躯体上的疾病。药物、毒品和酒精可以暂时缓解或消除无法忍受的感觉,但身体会记录着。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解释玛莎的扫描结果,而以下的每一项都给我们应该如何治疗带来启示。我们可以选择关注她的神经化学和生理状况异常:当玛莎在想起她女儿的死时,她的大脑明显处在化学不平衡的状态中。我们可以寻找一种化合药物,帮助玛莎缓解这种化学不平衡的反应,或者最好让她的大脑恢复平衡。根据我们扫描结果,我的一些在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的同事开始寻找药物,帮助人们更能够耐受高水平的肾上腺素。
我们也发现,玛莎对她过去的记忆高度敏感,因此,最好的治疗方式也许是某种脱敏治疗。反复向治疗师回顾自己的创伤细节后,她对于创伤的生理反应也许可以缓解,这样她就能理解,“那时是那时,现在是现在”,而不是一次次反复地体验过去的经历。
100多年来,几乎每一本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书籍都建议一种方式:通过谈论痛苦来缓解痛苦。然而,我们发现,创伤性经历已经反复促使人们重新体验痛苦。无论我们变得多么成熟、多么有洞察力,我们的理性大脑仍然需要把我们的情绪化大脑表达出来。我很惊讶,那些有过无法言喻的痛苦经历的人几乎不能谈及他们经历的核心。对于他们来说,描述他们发生过什么、简单地叙述一个受害者或者复仇者的故事,比理解、感受、将他们的内在体验变成外显的文字要容易许多。
我们的扫描结果表现了人们的创伤体验如何被日常生活的各方面激活。他们没有将过去的经历融入他们的生活之中。他们一直都在“过去”而无法回到“当下”,他们无法在现实中感到活力。
3年后,玛莎成了我的病人。我成功地用EMDR治愈了她。
(本文节选自《身体从未忘记》,作者 Bessel van der Kolk M.D)
版权声明:标注来源“心灵花园”为原创,版权所有。本站部分资源来自互联网,转载之目的为学术交流与讨论,如因转载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
Copyright © 2010-2017 TSPSY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