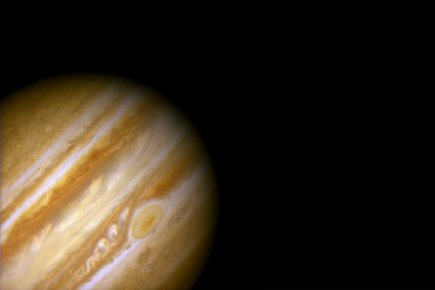心理疾病:医生也需要做治疗吗?
发表于 2018-10-15 14:20
心理导读:当我在1972年完成住院实习以后,我走上了两条同样诱人的职业路径——学院精神科工作和私人开业治疗师,它们在很多方面互为补充。为医学学生和住院实习生讲授精神医学课程和进行家庭诊疗,使我能够与时俱进地接触医学院和研究生培训中介于专业发展和个人成长之间的很多问题。 ---www.tspsy.com

心理疾病:医生也需要做治疗吗?
在过去21年的精神病学工作中,我成了医生的医生(Myers,1992a,1994)。然而,我对医生及其情绪困扰和精神困惑的兴趣,却开始得更早,而且是由悲剧事件所引发的。那是在1962年,我在医学院的室友自杀了。当时我并没有真正把他的死放在心上——我一直在解剖学实验室、生物化学实验和大学生联谊会活动之中忙忙碌碌。直到我在精神科住院实习期间(1969-1972)开始照看接受住院治疗的医生们(以及他们的配偶和孩子),我才开始审视照料这些患者对我个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记得那是种五味杂陈的情绪状态但是主要是焦虑和自我意识的感受。由于接受训练期间产生的这种心神不定的感觉,我知道,在为与医学领域毫不相干的患者提供治疗时,我会对自己的专业素养更加自信。
当我在1972年完成住院实习以后,我走上了两条同样诱人的职业路径——学院精神科工作和私人开业治疗师,它们在很多方面互为补充。为医学学生和住院实习生讲授精神医学课程和进行家庭诊疗,使我能够与时俱进地接触医学院和研究生培训中介于专业发展和个人成长之间的很多问题。身为本科精神医学教育负责人,我不仅能够了解学生们对教学问题的想法,还可以了解他们对医学院和医院里的学习风的关注。身为未来医生的教师兼管理者,我怎么可能不关心那些关于乏味的教学、虐待医学学生(Richmantaal,1992)、性骚扰(Charney&.Rusell,1994)以及我们医学中心如此之多的医生萎靡不振(Belkin,1993;Wehbe,1994)的情况的报告呢?
在我的私人医务所中,我既是个人治疗师又是专攻婚姻和离婚治疗的专家,有机会治疗大量遭受精神疾病折磨的医学学生、医生以及他们的家人。这成了一种特殊条件—因为当今的医生们所面临的那些生理上的和社会心理上的很多弱点,我也身在其中。能够帮助医学领域的人们重新感觉良好并再次发挥最大作用,这令我感到欣慰。但是这种工作也会深深地触到我的痛处,并激起大量烦扰和不安的情绪反应。
在这种背景下,继之而来的是我作为医生们的精神科医生的工作所特有的那些感受反思和洞见。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已经为大约500名前来找我咨询的医学学生和医生们提供了服务。他们的问题形形色色,既有重大精神疾患(双向情绪障碍、精神分裂症、周期性情绪障碍、智力衰退),也有比较轻微的顾虑,比如适应障碍、性功能失调和生活各阶段的问题,包括很多人对人际关系、婚姻和离婚的担忧。然而,潜藏在这些诊断类别之下的,或者说从中产生的,是医生们很多痛苦的情感冲突(例如,因病休假而产生的负疚感,依赖镇静剂而产生的羞耻感,对感染AIDS的焦虑感,婚姻走到尽头的失败感)。所有的治疗师都知道那些精神病学标签,而冷冰冰的诊断类别并不能够触及我们的患者们所遭受的内心的困扰。下面是一此触动治疗师心灵的“素材”。
震惊是很多精神科医生不常感受到的一种情绪反应,尤其是随着他们年龄渐长并且经验日渐丰富。他们往往会感觉到“我早就见识过了”。但是我作为一名医生们的精神科医生,确实不止一次地感受到了这种情绪,尽管我渐渐变得经验老到、身经百战。这里有一个例子:
当A医生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问我愿不愿接收他作为患者的时候,我起初很犹豫。为什么?有三个原因。首先,我们在同一所教学医院担任临床教学任务(尽管在不同的科室),并且都在一个AIDS政策委员会任职。其次,我们的妻子是朋友,尽管我们两对夫妻从来没有一起参加过社交活动。再次,我们的孩子们通过各种体育运动队而相互认识。我本想对A医生敷衍了事,但是他打消了我的想法,他在电话里说道:“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打这个电话,承认我需要帮助很令人尴尬,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打给你的,因为我曾经见过你,对你了解一点点,而且很尊重你胜过了这里的绝大多数精神科医生和我个人所了解的其他人。”奉承归奉承,我还是决定那个星期稍后一些和A医生会面。
因为我通过妻子了解到A医生的父亲最近刚刚去世,而且这对他来非常难以承受,所以我以为他打电话给我就是为了这个。错!他初次造访开场就说道:“谢谢你答应为我诊治。让我直说了吧。我不爱萨拉Sarah)。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爱过她。大约两年前我开始与我的秘书相爱并开始约会。现在她已经离开了她丈夫,而我也计划鼓起勇气告诉萨拉以后尽快与她离婚。莫尼卡(Monics)和我打算一起生活。我知道你做了很多婚姻和离婚方面的工作。你能帮忙吗?”
由于我先前对他的婚姻的了解和错误假设,当A医生告诉我他来看我的原因时,我被惊呆了。假如他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我倒不会感到震惊。同情会有的,但是震惊不可能。A医生在第一次造访的时候是如此的紧张和专注自我,我认为我的震惊他没有看出来。就算他看出来了,他也什么都没说。假如他说起来的话我会承认我的惊讶,给他作出简短的解释,然后继续进行评估。我发现,在初次会面以后,我作为他的治疗师不再那么窘迫了。我能够恢复往常的专业风范,并为他提供关怀支持、建议和指导。当他向他妻子表露离婚的计划时,他告诉她自己咨询了一位精神科医生,但是没有告诉她自己去看的是谁。我继续单独约见他,并推荐了一位治疗师,是他们两人都不认识的一位社会工作者,以便让他们两人接受离婚治疗。
(作者:麦克尔·F·迈尔斯 | 来源:危险的心理咨询)
版权声明:标注来源“心灵花园”为原创,版权所有。本站部分资源来自互联网,转载之目的为学术交流与讨论,如因转载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
Copyright © 2010-2017 TSPSY All Rights Reserved